《乡土中国》读书笔记-上(1-7章)
- 读书
- 2024-01-18
- 42
《乡土中国》—作者:费孝通
作者序言:
这本小册子的写作经过,在《后记》里已交代清楚。这里收集的是我在四十年代后期,根据我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而写成分期连载的十四篇文章。这本小册子的写作经过,在《后记》里已交代清楚。这里收集的是我在四十年代后期,根据我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而写成分期连载的十四篇文章。

第一章 | 乡土本色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
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地方一代一代地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Tönnies的话说:前者是Gemeinschaft,后者是Gesellschaft;用Durkheim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
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这自是“土气”的一种特色。因为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地在一个地方生下根,这些生了根在一个小地方的人,才能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像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般。陌生人对于婴孩的话是无法懂的,但是在做母亲的人听来都清清楚楚,还能听出没有用字音表达的意思来。
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第二章 | 文字下乡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关于病和贫我们似乎还有客观的标准可说,但是说乡下人“愚”,却是凭什么呢?乡下人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地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司机拉住闸车,在玻璃窗里,探出半个头,向着那土老头儿,啐了一口:“笨蛋!”——如果这是愚,真冤枉了他们。我曾带了学生下乡,田里长着包谷,有一位小姐,冒充着内行,说:“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旁边的乡下朋友,虽则没有啐她一口,但是微微地一笑,也不妨译作“笨蛋”。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一般。如果我们不承认郊游的仕女们一听见狗吠就变色是“白痴”,也就自然没有理由说乡下人不知道“靠左边走”或“靠右边走”等时常会因政令而改变的方向是因为他们“愚不可及”了。“愚”在什么地方呢?
可是如果说不识字就是愚,我心里总难甘服。“愚”如果是指智力的不足或缺陷,那么识字不识字却并非愚不愚的标准。智力是学习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还是学不到什么的。我们是不是说乡下人不但不识字,而且识字的能力都不及人呢?
乡下孩子在教室里认字认不过教授们的孩子,和教授们的孩子在田野里捉蚱蜢捉不过乡下孩子,在意义上是相同的。乡下人是否在智力上比不上城里人,至少还是个没有结论的题目。
在“面对面的社群”里甚至可以不必见面而知道对方是谁。在“面对面的社群”里一起生活的人是不必通名报姓的。“贵姓大名”是因为我们不熟悉而用的。熟悉的人大可不必如此,足声、声气甚至气味,都可以是足够的“报名”。我们社交上姓名的不常上口也就表示了我们原本是在熟人中生活的,是个乡土社会。
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需要结绳来记事是为了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我们不能当面讲话,才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
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这不完全是出于“间接接触”的原因。我们所要传达的情意是和当时当地的外局相配合的。你用文字把当时当地的情意记了下来,如果在异时异地的圜局中去看,所会引起的反应很难尽合于当时当地的圜局中可能引起的反应。文字之成为传情达意的工具常有这个无可补救的缺陷。于是在利用文字时,我们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文法和艺术就在减少文字的“走样”。
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当我们有了电话、广播的时候,书信文告的地位已经大受影响。等到传真的技术发达之后,是否还用得到文字,是很成问题的。这样说来,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了。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在面对面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语言本是用声音来表达的象征体系。象征是附着意义的事物或动作,我说“附着”是因为“意义”是靠联想作用加上去的,并不是事物或动作本身具有的性质。这是社会的产物,因为只有在人和人需要配合行为的时候,个人才需要有所表达;而且表达的结果必须使对方明白所要表达的意义。所以象征是包括多数人共认的意义,也就是这一事物或动作会在多数人中引起相同的反应。因之,我们绝不能有个人的语言,只能有社会的语言。要使多数人能对同一象征具有同一意义,他们必须有着相同的经历,就是说在相似的环境中接触和使用同一象征,因而在象征上附着了同一意义。因此在每个特殊的生活团体中,必有他们特殊的语言,有许多别种语言所无法翻译的字句。
“特殊语言”常是特别有效,因为它可以摆脱字句的固定意义。语言像是个社会定下的筛子,如果我们有一种情意和这筛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过去。
于是在熟人中,我们话也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中去批判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因为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而且这工具本身也是有缺陷的,能传的情、能达的意是有限的。所以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
第三章 | 再论文字下乡
人的“当前”中包含着从“过去”拔萃出来的投影,时间的选择累积。一个依本能而活动的动物不会发生时间上阻隔的问题,它的寿命是一连串的“当前”,谁也不能剪断时间,像是一条水,没有刀割得断。但是在人却不然,人的当前是整个靠记忆所保留下来的“过去”的累积。如果记忆消失了、遗忘了,我们的“时间”就可说是阻隔了。
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还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可或缺的生活基础。人不能离开社会生活,就不能不学习文化。文化得靠记忆,不能靠本能,所以人在记忆力上不能不力求发展。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
在一个乡土社会中生活的人所需记忆的范围和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是不同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生于斯,死于斯”的结果必是世代的黏着。这种极端的乡土社会固然不常实现,但是我们的确有历世不移的企图,不然为什么死在外边的人,一定要把棺材运回故乡,葬在祖茔上呢?一生取给于这块泥土,死了,骨肉还得回入这块泥土。
时间的悠久是从谱系上说的,从每个人可能得到的经验说,却是同一方式的反复重演。同一戏台上演着同一的戏,这个班子里演员所需要记得的,也只有一套戏文。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
在都市中生活,一天到晚接触着陌生面孔的人才需要在袋里藏着本姓名录、通信簿。在乡土社会中黏着相片的身份证,是毫无意义的。在一个村子里可以有一打以上的“王大哥”,绝不会因之错认了人。都市社会里有新闻;在乡土社会,“新闻”是稀奇古怪、荒诞不经的意思。在都市社会里有名人,乡土社会里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不为人先,不为人后,做人就得循规蹈矩。这种社会用不上常态曲线,而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套。
在这种社会里,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然能在一个比他年长的人那里问得到解决这问题的有效办法,因为大家在同一环境里,走同一道路,他先走,你后走;后走的所踏的是先走的人的脚印,口口相传,不会有遗漏。哪里用得着文字?时间里没有阻隔,拉得十分紧,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
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一直到目前还不是我们乡下人的东西。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
第四章 | 差序格局
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是“私”。说起私,我们就会想到“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的俗语。谁也不敢否认这俗语多少是中国人的信条。其实抱有这种态度的并不只是乡下人,就是所谓城里人,何尝不是如此。
所谓“私”的问题却是个群己、人我的界限怎样划法的问题。我们传统的划法,显然是和西洋的划法不同。因之,如果我们要讨论私的问题就得把整个社会结构的格局提出来考虑一下了。
西洋社会组织像捆柴就是想指明: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得分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事先规定的。我用捆柴来比拟,有一点不太合适,就是一个人可以参加好几个团体,而好几扎柴里都有某一根柴当然是不可能的,这是人和柴不同的地方。我用这譬喻是在想具体一些,使我们看到社会生活中人和人的关系的一种格局。我们不妨称之作团体格局。
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如果有一位朋友写信给你说他将要“带了他的家庭”一起来看你,他很知道要和他一同来的是哪几个人。在中国,这句话是含糊得很。在英美,家庭包括他和他的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如果他只和他太太一起来,就不会用“家庭”。在我们中国“阖第光临”虽则常见,但是很少人能说得出这个“第”字究竟应当包括些什么人。提到了我们的用字,这个“家”字可以说最能伸缩自如了。“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伯叔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
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
当我们用这体系来认取具体的亲亲戚戚时,各人所认的就不同了。我们在亲属体系里都有父母,可是我的父母却不是你的父母。再进一步说,天下没有两个人所认取的亲属可以完全相同的。兄弟两人固然有相同的父母了,但是各人有各人的妻子儿女。因之,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来说,是个别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
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
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像个小国。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
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
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释名》于伦字下也说“伦也,水文相次有伦理也”。潘光旦先生曾说:凡是有“仑”作公分母的意义都相同,“共同表示的是条理、类别、秩序的一番意思”。(见潘光旦《说伦字》,《社会研究》第十九期)
伦重在分别,在《礼记·祭统》里所讲的十伦: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都是指差等。“不失其伦”是在别父子、远近、亲疏。伦是有差等的次序。在我们现在读来,鬼神、君臣、父子、夫妇等具体的社会关系,怎能和贵贱、亲疏、远近、上下等抽象的相对地位相提并论?其实在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概念,这个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礼记·大传》里说:“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意思是这个社会结构的架格是不能变的,变的只是利用这架格所做的事。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纹波浪向外扩张的推字。他先承认一个己,推己及人的己,对于这己,得加以克服于礼,克己就是修身。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就可向外推了。“本立而道生”。“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中庸》里把五伦作为天下之达道。因为在这种社会结构里,从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所以孟子说他“善推而已矣”。
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个人是对团体而说的,是分子对全体。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煞个人,只能在个人们所愿意交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这些观念必须先假定了团体的存在。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
自我主义并不限于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杨朱,连儒家都该包括在内。杨朱和孔子不同的是杨朱忽略了自我主义的相对性和伸缩性。他太死心眼儿一口咬了一个自己不放;孔子是会推己及人的,可是尽管放之于四海,中心还是在自己。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是很好的一个差序格局的譬喻,自己总是中心,像四季不移的北极星,所有其他的人,随着他转动。孔子并不像耶稣,耶稣是有超于个人的团体的,他有他的天国,所以他可以牺牲自己去成全天国。孔子呢,不然。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孔子的道德系统里绝不肯离开差序格局的中心,“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因之,他不能像耶稣一样普爱天下,甚至而爱他的仇敌,还要为杀死他的人求上帝的饶赦——这些不是从自我中心出发的。孔子呢?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是差序层次,孔子是绝不放松的。孔子并不像杨朱一般以小己来应付一切情境,他把这道德范围依着需要而推广或缩小。他不像耶稣或中国的墨翟,一放不能收。
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在西洋社会里,国家这个团体是一个明显的也是唯一特出的群己界线。在国家里做人民的无所逃于这团体之外,像一根柴捆在一束里,他们不能不把国家弄成个为每个分子谋利益的机构,于是他们有革命、有宪法、有法律、有国会等等。在我们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之家,界限从来就是不清不楚的,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的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所以可以着手的,具体的只有己,克己也就成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性,他们不会去克群,使群不致侵略个人的权利。在这种差序格局中,是不会发生这问题的。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第五章 | 系维着私人的道德
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我所谓“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从社会观点说,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使他们合于规定下的形式行事,用以维持该社会的生存和绵续。
在以自己作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最主要的自然是“克己复礼”,“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出发点。社会范围是从“己”推出去的,而推的过程里有着各种路线,最基本的是亲属: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向另一路线推是朋友,相配的是忠信。“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孔子曾总结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差序格局中并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这种超己的观念必须在团体格局中才能发生。孝、悌、忠、信都是私人关系中的道德要素。
不但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没有一个像基督教里那种“爱”的观念——不分差序的兼爱;而且我们也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在西洋团体格局的社会中,公务,履行义务,是一个清楚明白的行为规范。而这在中国传统中是没有的。现在我们有时把“忠”字抬出来放在这位置上,但是忠字的意义,在《论语》中并不如此。我在上面所引“为人谋而不忠乎”一句中的忠,是“忠恕”的注解,是“对人之诚”。“主忠信”的忠,可以和衷字相通,是由衷之意。
团体道德的缺乏,在公私的冲突里更看得清楚。就是负有政治责任的君王,也得先完成他私人间的道德。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
团体格局的社会里,在同一团体的人是“兼善”的,就是“相同”的。孟子最反对的就是那一套。他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墨家的“爱无差等”,和儒家的人伦差序,恰恰相反,所以孟子要骂他无父无君了。
第六章 | 家族
比较确当的应该称中国乡土社会基本社群作“小家族”。
家庭既以生育为它的功能,在开始时就得准备结束。抚育孩子的目的就在结束抚育。
在西洋,家庭是团体性的社群,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说明有严格的团体界限。因为这缘故,这个社群能经营的事务也很少,主要的是生育儿女。可是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这社群里的分子可以依需要,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构成这个我所谓社圈的分子并不限于亲子。但是在结构上扩大的路线却有限制。中国的家扩大的路线是单系的,就是只包括父系这一方面;除了少数例外,家并不能同时包括媳妇和女婿。在父系原则下女婿和结了婚的女儿都是外家人。在父系方面却可以扩大得很远,五世同堂的家,可以包括五代之内所有父系方面的亲属。
这种根据单系亲属原则所组成的社群,在人类学中有个专门名称,叫氏族。我们的家在结构上是一个氏族。家族在结构上包括家庭;最小的家族也可以等于家庭。因为亲属的结构的基础是亲子关系,父母子的三角。家族是从家庭基础上推出来的。但是包括在家族中的家庭只是社会圈子中的一轮,不能说它不存在,但也不能说它自成一个独立的单位,不是一个团体。
家族虽则包括生育的功能,但不限于生育的功能。依人类学上的说法,氏族是一个事业组织,再扩大就可以成为一个部落。氏族和部落赋有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的功能。我们的家也正是这样。我的假设是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使这基本的家,变成氏族性了。
这个基本社群绝不能像西洋的家庭一般是临时的。家必须是绵续的,不因个人的长成而分裂,不因个人的死亡而结束,于是家的性质变成了族。氏族本是长期的,和我们的家一般。我称我们这种社群作小家族,也表示了这种长期性在内,和家庭的临时性相对照。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家的大小是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的。如果事业小,夫妇两人的合作已够应付,这个家也可以小得等于家庭;如果事业大,超过了夫妇两人所能担负时,兄弟伯叔全可以集合在一个大家里。这说明了我们乡土社会中家的大小变异可以很甚。但不论大小上差别到什么程度,结构原则上却是一贯的、单系的差序格局。
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性质在这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我们的家既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配轴虽则和主轴一样并不是临时性的,但是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我所谓普通的感情是和纪律相对照的。一切事业都不能脱离效率的考虑。求效率就得讲纪律;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在中国的家庭里有家法,在夫妇间得相敬,女子有着三从四德的标准,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这些都是事业社群里的特色。
不但在大户人家,书香门第,男女有着阃内阃外的隔离,就是在乡村里,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现象。我在乡间调查时特别注意过这问题,后来我又因疏散下乡,和农家住在一所房子里很久,更使我认识了这事实。我所知道的乡下夫妇大多是“用不着多说话的”,“实在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一早起各人忙着各人的事,没有工夫说闲话。出了门,各做各的。妇人家如果不下田,留在家里带孩子。工做完了,男子们也不常留在家里,男子汉如果守着老婆,没出息。有事在外,没事也在外。茶馆,烟铺,甚至街头巷口,是男子们找感情上安慰的消遣场所。在那些地方,大家有说有笑,热热闹闹的。回到家,夫妇间合作顺利,各人好好地按着应做的事各做各的。做得好,没事,也没话;合作得不对劲,闹一场,动手动脚,说不上亲热。这些观察使我觉得西洋的家和我们乡下的家,在感情生活上实在不能并论。乡下,有说有笑,有情有意的是在同性和同年龄的集团中,男的和男的在一起,女的和女的在一起,孩子们又在一起,除了工作和生育事务上,性别和年龄组间保持着很大的距离。这绝不是偶然的,在我看来,这是把生育之外的许多功能拉入了这社群中去之后所引起的结果。中国人在感情上,尤其是在两性间的矜持和保留,不肯像西洋人一般地在表面上流露,也是在这种社会圜局中养成的性格。
第七章 | 男女有别
纪律排斥了私情。这里我们碰着了中国传统感情定向的基本问题了。
我用感情定向一词来指一个人发展他感情的方向,而这方向却受着文化的规定,所以在分析一个文化型式时,我们应当注意这文化所规定个人感情可以发展的方向,简称作感情定向。
如果要维持固定的社会关系,就得避免感情的激动。其实,感情的淡漠是稳定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示。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所谓了解,是指接受着同一的意义体系。同样的刺激会引起同样的反应。
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习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只有生于斯、死于斯的人群里才能培养出这种亲密的群体,其中各个人有着高度的了解。
男女生理上的分化是为了生育,生育却又规定了男女的结合。这一种结合基于异,并非基于同。在相异的基础上去求充分了解,是困难的,是阻碍重重的,是需要不断地在创造中求统一。男女的共同生活,愈向着深处发展,相异的程序也愈是深,求同的阻碍也愈是强大,用来克服这阻碍的创造力也更需强大。
依现代文化来看,男女间感情激动的发达已使生育的事业摇摇欲坠。这事业除非另外设法,由社会来经营,浮士德式的精神的确在破坏这社会上的基本事业。
在乡土社会中这种精神是不容存在的。它不需要创造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生下来就决定的。它更害怕社会关系的破坏,因为乡土社会所求的是稳定。男女间的关系必须有一种安排,使他们之间不发生激动性的感情。那就是男女有别的原则。“男女有别”是认定男女间不必求同,在生活上加以隔离。这隔离非但是有形的,所谓男女授受不亲,而且还是在心理上的,男女只在行为上按着一定的规则经营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的事业,他们不向对方希望心理上的契洽。
在社会结构上,如上篇所说的,因之发生了同性间的组合。这在我们乡土社会中看得很清楚。同性组合和家庭组合原则上是交错的,因为以生育为功能的家庭总是异性的组合。因之,乡土社会中“家庭”的团结受到了这同性组合的影响,不易巩固。于是家族代替了家庭,家族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中国乡土社会里,以家族为基本社群,是同性原则较异性原则为重要的表示。
男女有别的界限,使中国传统的感情定向偏于向同性方面去发展。变态的同性恋和自我恋究竟普遍到什么程度,我们无法确说;但是乡土社会中结义性的组织,“不愿同日生,但愿同日死”的亲密结合,多少表示了感情方向走入同性关系的一层里的程度已经并不很浅。在女性方面的极端事例是华南的姊妹组织,在女性文学里所流露的也充满着冯小青式的自恋声调。可惜我们对于中国人的感情生活太少分析,关于这方面的话我们只能说到这里为止了。
中国乡土社会中那种实用的精神安下了现世的色彩。儒家不谈鬼,“祭神如神在”,可以说对于切身生活之外都漠然没有兴趣。
社会秩序范围着个性,为了秩序的维持,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男女之间的鸿沟从此筑下。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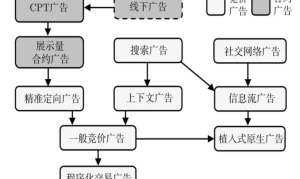

发表评论